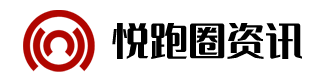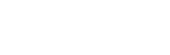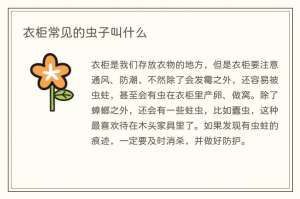还记得那一次童年趣事,母亲边经常带我去对面村庄的亲戚家串门,每每总能瞧见门口拴着一只大黄狗。而这只狗对主人十分听话,对外人却是呲牙咧嘴,若是没有主人的允许,誰都无法踏进他家半步。
而我却不怎么怕恶狗,那黄毛狗似乎也能读懂我的善意,总是对我吐舌头、摇尾巴,从来都不会对我凶恶。大娘见我如此喜欢狗,便对母亲说:“看你娃娃那么喜欢狗,就随便领一条小狗崽回去吧!”
还没等母亲回答,我就兴奋地拍着脑袋望着大娘道:“真的吗?”
大娘见我如此一本正经,露出慈善地笑容:“大娘说话算数”
我就领了一只毛茸茸的黑色狗崽,它的体积大不了多少,比刚出生的幼婴还要小得多,估计体质再一小点都能放进裤兜儿了。
抱着小狗儿火箭般地回家,弟弟早已在家恭候多时了,他激动地想要过来抱抱小狗,像是警铃一下震响般,很快弟弟的手臂多了一道浅浅的血痕。
弟弟疼得快要哭了出来,没想到可爱的小狗居然如此凶悍,直接将弟弟咬了一口,幸好幼年的狗崽犬牙不是很成熟,否则弟弟的手都被它咬掉一块皮。
母亲见状赶紧找来以前拴狗的铁链,准备要套在小黑狗的脖颈上,小狗像是感知到危险一样,冲着母亲呲牙咧嘴,还未张齐的犬牙也显露出来,发出凶恶的警告声。
差一点就要咬到母亲的手,我便轻轻抚摸着狗的额头,让它舒服地吐出舌头,尾巴不由自主地随风而舞。
很快,狗的脖颈处留下铁链的痕迹,它开始限制了身体的自由,连呼吸也是如此的压抑。
我看不出母亲满脸皱纹上的表情,只瞧见她用满是沾满泥土的大手将狗房子后院里去。那是正砌了一两面断墙的地基,而小狗则被核桃树判了刑期。
吃晚饭过后,我便端了一碗杂烩面放到小黑狗的碗跟前,小狗崽吃得很缓慢,好像食物全部卡在脖颈里了。随后央求弟弟找来一个啤酒纸箱,去伙房找来了几张干燥的苞谷叶放进去,做成了简陋的狗窝。
这次小狗崽伸出粉嫩的软舌,亲切地刮了刮弟弟的手,并不停地向弟弟“哈哈”气,似乎是对弟弟放弃了警惕性。
渐渐地,太阳开始又大又圆,晒得黄皮果树上的果肉变成熟了,也懒得将天空镀成金黄色。一片片绵云层层叠叠的,又厚又重,很块将背包也一起带来。
跟小狗崽相处一段时间,它成功地陪伴我和弟弟很久,这小家伙也是非常聪明,从不把大小便留在屋里或床上,一般都会在外头地杂草丛方便。
因为它全身都是通黑的,毛发都是跟黑色沾边的,于是我就给它取名为“黑宝儿”。
黑宝儿对我来说如此地喜欢,对它也是伶人生爱,慢慢地也开始接受家人的存在,只不过体积还是处于婴儿般的状态。
凡是在僻壤的乡下,要是用来养狗的话。它的工作任务只有一个,那就是看家护院,才能让它在屋子包吃包住,但事情往往是节外生枝。
黑宝儿依旧幼小可楚,它这样子是无法看家,没有利用的价值意义,就跟丢了工作的无业游民一样,成为了家庭的被遗弃者。
以至于后来,国庆七天的时候我再也无法看到黑宝儿的身影,只剩下一条锈迹斑驳的拴狗链。哪天正好姨妈带着她女儿来耍,桌上不知多了来路不明的狗肉,也送到我的胃里消化了。
我成为了“黑宝儿”的刽子手,手里占满了它的狗血。那血还是热灬的,飘散出呕作的腥味。
弟快要将肺都哭出来,近段时间以来我好久都没养过宠物。
直到某天放晚学后,我带着顽伴到附近的小河道里嬉闹,偶然发现邻居家的小孩将一条纯白小狗“玩水”。小白狗被呛得快要咽气了,白花花的肚皮灌满了河水,就像肿胀的皮球一样,用一根细花针戳估计就得爆水了。
看那小孩如此劣性,我便对他大喝一声:“住手!你为什么要淹死小狗”
小孩剜了我一眼:“这条狗太可恶了,都不听我的话,我就是要把它淹死”
话音刚落,他又让白狗喝了几口河水。我赶忙阻止他:“反正你也不想养了,不如我用一罐弹珠跟你换吧”
因为弹珠在小朋友之间,是非常的珍贵的宝藏,邻居的小孩没都没想就同意了,跑回家的我拿出床底下一罐弹珠,直接跟邻居小孩两手换物。
快要进鬼门关的小白狗在我手里痛苦地哀嚎着,我一脸焦虑地拍了狗的背部。直到肚皮瘪下去时,便小心翼翼抒着它的肚子,折腾了好久,总算把小白狗肺里和肚子里的水排差不多了。可是,当我放它到地上时,小白狗还是像喝醉酒似的,东倒西歪走不稳路。
唉!小白狗是救下来了,但又送给谁养呢?顽伴们纷纷编事推脱,但不能随便将它遗弃在外,只好发起善心带回家里。
虽然老弟再次兴奋激动,可为此和父母争吵大闹。尤其是父亲,他是最反对养宠物的行为,主要原因还是粮食问题,当时螚天天吃上米饭都算是中等水平了。
有一次,父亲手錂着小白狗扔到一处小豆坡里,被我和弟弟直接给找回来了。几番下来,父亲最终败给了我跟弟弟的毅力。
这次我给小白狗取名为“白宝”,因长着一身雪白的绒毛,像白绸子一样油亮光滑;露出那雪白的软爪子,如梅状的雪花一样,那小尾巴也是雪白雪白的,撅起来不停向你左右摆动。
白宝是如此乖巧的,没有灰宝儿的那种凶性,有时也会在野山密林逮一只竹鼠和野兔,叼回来給我们改善伙食。
只不过后来我上中学后,基本是很少回家的。等节假日的时候回来,才知道白宝经常食不果腹,最后成为父亲的下酒菜。
我又再次成为了白宝的“凶手”,无法让它生老病死,只祈求天堂能够收留它们。直到大学毕业后,再也没养过一次宠物。